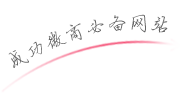- 首页
- 微信群
微信群大全 创业群 辣妈群 互粉群 微信福利群 微信红包群 麻将群
- 地区微信
- 个人微信
微商微信 模特微信 交友微信 宝妈微信 女性微信 吃货微信- 微信公众号
微商公众号 搞笑公众号 教育公众号 兼职公众号 娱乐公众号 营销公众号 电商公众号- 微信货源
忆奶奶的一生
发布人:微信群 / 发布时间2018-12-29 热度:我的奶奶是个慈祥的老人,虽然已经七十多岁,长着一头银白色的头发,经过流水般的岁月,奶奶的脸上已有许多的皱纹,好像刻着几十年
我的奶奶是个慈祥的老人,虽然已经七十多岁,长着一头银白色的头发,经过流水般的岁月,奶奶的脸上已有许多的皱纹,好像刻着几十年来的千辛万苦。
奶奶年轻时的照片在过去流亡生涯中全部遗失。但是,下雪的那个早上,我又一次让自己肯定了奶奶少女时代那超凡脱俗的美丽。我曾不止一次想象着美丽的奶奶冲出闺阁的小楼,穿着白色裙裾,不顾曾祖父、曾祖母的反对,翩翩迈进女子师范学校时的风姿。我曾白去流水似的想象,奶奶与英俊潇洒的军官爷爷相遇相亲相爱,并结为连理的浪漫情怀,我甚至大胆地假设,奶奶与爷爷一定是在雪地里相识的,在我想到这一点时,我清楚地感觉到那两道目光碰撞的那一瞬间的震颤。我难以想象的是,在爷爷早逝不久,奶奶坚强地满怀悲怆生下遗腹子——我父亲时的景况。
失去了爷爷的奶奶,从此住在一幢大房子里,靠她丰厚的嫁妆和国民党军官爷爷留下的遗产,潜心培育着父亲,直到解放后,奶奶的房产被政府没收,她搬进平民区,从此便过起俭朴的日子。光景不长,这种自食其力的平淡日子便被打破了,随着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及运动的频频席卷,奶奶和父亲开始了流浪生涯。具有双重坏出身的父亲,这时理所当然地成了挨批挨斗挨整的改造对象。父亲遭批判,奶奶便每天跟着他走街串巷陪斗。看儿子在台上被人鞭打侮骂,奶奶便用针刺着自己的大腿,仿佛这样便可将父亲身上的疼痛转移到自己身上。父亲在很长时间内不知道,当他得知这事以后,曾跪在奶奶的面前将他这一生的眼泪都哭干了,直到奶奶死,他也没有落过一颗泪。父亲像老鼠被猫玩够了,那些人便将奶奶和父亲下放到北方一个偏僻的乡村,住在一间茅草棚里相依为命。
在这个叫高岭的小村里,于深闺书香中长大的奶奶开始学着做各种农活:养鸡、种地、挖野菜,过着往往只有在米饭中夹着野菜、番薯、豆类等,才得一饱的日子。奇怪的是,在那群山起伏、鸡犬相闻的宁静中,奶奶比以前更加丰润美丽起来,岁月的风霜一点也没有摧去她那美丽的气韵与高贵的风范。甚至奶奶养的鸡也比别人养的鸡下蛋勤,奶奶种的白菜萝卜个头也比别人家的大。奶奶的这份美丽,很快使得自己必须带着父亲第二次踏上流浪生涯。
奶奶并不惧怕强人。村里的支部书记曾数次将父亲安排去看地瓜或修水利,然后便在一个深夜来到奶奶的茅草屋里坐下来。一开始是以将奶奶安排到村里的仓库去住为利诱,随着便是有权有势的男人对付弱妇子惯用的强暴。奶奶用她那只纤细的手抽了他一个耳光,再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滚!那种气质的力量,使得他再也不敢上门。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周围的老人几乎都是不识字的,唯有奶奶是个例外。奶奶不仅识字而且还挺有学问。上小学时,有一阵我怎么也分不清鲜和艳字,总是将它们搞混了,用鲜作艳,用艳作鲜。为这事奶奶揪着我的小耳朵说过几次,可我仍然转眼就忘了。
那一回,当我又写错了以后,奶奶真的生气了,罚我将每个字写500遍。我哭哭啼啼的半夜才写完。一直没作声的奶奶,这时将我拉到怀里,一边给我洗脸,一边对我说:“饿了吗,想吃什么?”我说:“不想吃!”奶奶说:“那就喝点汤。”奶奶说着就端一碗汤,我尝了一口,味道真是好极了。我问奶奶这是什么汤,奶奶让我猜。我猜了半天没猜着。奶奶这才告诉我,说这是用鱼肉和羊肉混合后做的汤。奶奶说,鲜吗?我说,真鲜。奶奶说,你再想想它为什么鲜,因为它是用鱼和羊做的!奶奶这解释真是妙极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错鲜艳二字。奶奶是在雪花飘飘的季节来到这个世上,又在雪花飘飘的静谧里安详地长睡而去。奶奶一生对雪如痴如醉,常常让我在观她时亦如痴如醉。奶奶临去前的那个冬天,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雪是从头天傍晚时开始落下的,望着鹅毛雪片,奶奶用一种我从未听见过的娇柔的声音轻轻地自语:明早可以睡个懒觉了。我相信这话不是对我们说的,而是说给那个已随岁月远去的人。第二天早上醒来层里不见奶奶,开门后,见一行脚印孤零零地伸向雪野,在脚印的那一端,包着红头巾的奶奶,化作一个小红点,无声无息地伫立着。家里人都没去惊动她,甚至连她踏过的雪地也不去打扰,任软茸茸的一串小小脚窝,几分优美,几分凄婉地搁在那里。
这就是我的奶奶,操劳了一生,勤劳了一生,坎坷了一生,历尽苦难而沧桑了一生。
上一篇: 最冷的冬天已经过去,春天来了 下一篇: 岁月流逝,初心未变分享到朋友圈
 精选文章
精选文章- 03-28 再现学霸寝室,6人全部保研成功
- 03-28 你不得不知道,房产税要出新规定了
- 03-28 听说华为要做电视了?
- 03-28 蛋壳公寓忽视消费者生命
- 03-28 林妙可合影显大气
- 03-28 注意,我们的假期可能要有变化啦
- 03-28 “幸运盒子”真的幸运吗?
- 03-28 baby登美国杂志与黑寡妇比美,谁胜谁负?
- 03-28 这样奇葩的事情还真多,母亲挥刀砍死了自
- 03-28 2019年3月28日,来看看今日的财经新闻
- 03-28 股市先驱之茅台酒业
- 03-28 新的增值税政策即将实行,还没买车的朋友
分享家规则

- 1、第一分享家好处是什么?
-
1)文章会挂上你的二维码提高爆光率
2)分享出去的文章你就是作者
3)将会获得网站金币
4)首页推荐快速加粉丝
5)像公众号一样传播你的文章
- 2、如何成功激活分享家?
- 任何微信搜索用户都可以成为分享家,您只要把任何一篇文章成功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必须是微信朋友圈,分享到其他平台是激活不了的哦),系统就会立即自动激活您成为分享家。
- 3、如何成为第一分享家?
- 第一分享家是分享家族中最高荣誉,在分享家族中分享同一篇文章贡献值最高的用户就是该文章的第一分享家。
- 4、怎样统计我的贡献值?
- 贡献值是来自您分享文章到微信朋友圈好友的访问量,访问IP次数越多,贡献值就越高。同样您朋友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您分享的文章,其贡献值也是属于您的。朋友帮您转发的越多,您的贡献值就会更高。
 保存图片后,随时访问手机端!
保存图片后,随时访问手机端!